作者:梦中梦789
2025/09/02发表于:SIS001
是否首发:是
字数:10,993 字
第一章
今年,按法兰克人的算法是1626年,按我们的迁徙历算,则是1035年。
我这天正好有空,走进了埃及亚历山大港一座我常去的咖啡馆。
店主向我介绍了一个看起来是红头发的中年人,他自称穆拉德·雷斯,原名
杨·杨松,以前是个荷兰的海盗船长,后来荷兰与西班牙议和后,他转投摩洛哥
海岸的萨利海盗共和国,并在那里颇有威望,但最近几年萨利共和国内讧不断,
他打算到埃及来通过贿赂获得至高帝国的正式委任,以强化自身地位,靠帝国权
威压制内部政敌。
他向咖啡厅店主打听后,得知我正好在给亚历山大港的至高帝国海军掌旗官
做卫兵,由于我这几年来多次参加埃及舰队与基督徒海盗的作战,屡次和同伴击
退了海盗发起的跳帮作战,保护了掌旗官的安全,因此颇受信任,正好适合引荐
给亚历山大港的帝国海军掌旗官。
杨松还和我说起,他通过俘虏的一个挪威船员,得知了冰岛因为地处偏远而
疏于防备,希望明年夏天发起的这次冰岛远征能为他建立威名,进一步强化他在
萨利共和国的地位。
杨松这番话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我出身鲁梅里亚的西帕西领主家族,是
家中第五个儿子,注定无法继承家业,在接受了家族能提供的多年军事训练后,
带着一张弓和一匹骡子外出闯荡,和我同行的几个伙伴自嘲:「像我们这种提马
尔家的小儿子,只能给耶尼切里扛旗」,但现在帝国与各方敌人的摩擦不断,从
军和发财的机会还是不少的。
我想起姐姐法蒂玛跟随一船的人,从萨洛尼卡乘船去亚历山大港,要去红海
边的两圣地朝圣时,遭遇了异教徒海盗的袭击,那是一伙自称医院骑士团的海盗,
听说他们把我姐姐贴上了土耳其女人的标签,卖到了意大利为奴,从此我再也没
见过她。
于是我下定决心加入了帝国海军的埃及舰队,希望能打探到姐姐的下落。
我到亚历山大后,船上的熟人介绍我把骡子卖给一个希腊人老铁匠,他给了
我一柄二手波斯弯刀,刀面磨掉了前主人的名字,只留一行「愿真主恩赐胜利」。
我从普通的船上弓箭手做起,五六年来历经大小十余次战斗,树立了自己的
些许名声,被掌旗官选中做他的侍从。
回想往事,我在埃及生活的这几年,虽然收到了不少赏赐,生活富裕,但难
免觉得十分孤独,并被本地人多有排斥,当地埃及人把我视为从北方来的鲁姆人,
常把对帝国征税的不满转化成对我的冷眼相待。
因此我也希望能通过新的冒险填补心理的空虚。
于是同意了为杨松引荐,并希望加入他的海盗团。
记得刚来埃及时我还曾请求掌旗官的书记官,替我查过马耳他来的俘虏名册,
几年前确有一名叫法蒂玛·阿普杜拉的女俘虏,年龄籍贯都对得上,后面写着她
在拿坡里被转卖了。
我想若不能救回姐姐,便让十字架下的女人也尝尝被锁链拖过甲板的滋味。
杨松船长向哈立德掌旗官送上劫掠来的数千金币和其他财物,掌旗官十分满
意,当即表示他会马上向帝国高门推荐杨松船长担任帝国的正式雷斯,委任状很
快就能准备好。
杨松进一步提出,能带几个人回去做帝国的代表更好,掌旗官会意地派了我
等几个人一起去,临行时对我们说:「等以后回来了,别忘了分享一下你们的冒
险故事,这值得帝国臣民为之传颂。」
离开亚历山大港后,我随穆拉德·雷斯乘船西行,沿马格里布海岸航行数周,
终于在1626年秋抵达摩洛哥的萨利海盗共和国。
海风夹杂着盐腥与港口的喧嚣扑面而来,萨利的景象既熟悉又陌生,这是一
座由海盗、叛军与冒险者共筑的混乱之城,表面繁荣,内里暗流涌动。
我立刻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紧张气氛,穆拉德·雷斯告诉我,萨利现在分裂为
两派:一派是忠于他的新海盗,多为荷兰、英格兰等欧洲国家的叛逃者,主张与
帝国保持松散联系以换取更大自由;另一派是本地摩洛哥人和从西班牙被驱逐的
摩尔人,主张就近依附摩洛哥王国以获取保护,两派互相争抢战利品分配和海盗
舰队的主导权。
穆拉德带我走进一间由旧堡垒改建的萨利城邦议会,二十余名海盗头目和当
地贵族围坐一圈,争吵不休,一名摩尔人拍桌怒吼:「你的冰岛远征是妄想,只
会浪费勇士的鲜血和我们宝贵的战船!」
穆拉德冷笑,掏出奥斯曼掌旗官的委任状,宣布自己已被帝国正式任命为帝
国海军的雷斯,承诺将战利品公平分配,并以帝国权威震慑反对者。
厅内短暂沉默,但我注意到几人眼中仍闪过不信任的光芒。
穆拉德私下对我说:「这张纸只能压住他们一时,冰岛远征必须成功,否则
我在这里很难立足。」
接下来的日子,萨利的港口忙碌异常,穆拉德的海盗团为冰岛远征做最后准
备。
他的舰队包括三艘主力船:旗舰「海狼号」,一艘改装自荷兰商船的快速帆
船,配备12门火炮;以及两艘较小的单桅船,适合近岸突袭。
船上那些炮手多是欧洲叛教者,言辞粗鲁但技术过硬。
穆拉德为远征召集了200 多名海盗,混合了摩洛哥人、欧洲叛逃者和少量帝
国雇佣兵。
他们聚集在港口附近的沙滩上操练,练习跳帮作战。
一天夜深人静,穆拉德召集众人,宣布远征将在来年夏初启航,目标是冰岛
的丰饶渔村与无防备的港口,冰岛以前从未被帝国海军所触及过,这次探险的范
围远超过以前帝国海军的活动范围,仅凭这点,能参加这次远征,就是前所未有
的壮举,为帝国海军增添了新的荣誉,我们必将因此而名扬天下,为后世传颂。
海盗们举起弯刀,高喊着真主的荣光与财宝的诱惑。
1627年夏初,萨利的港口烈日炙烤,穆拉德·雷斯的舰队终于扬帆起航,目
标直指冰岛。
三艘船,旗舰「海狼号」和两艘单桅船载着百余名海盗,乘着大西洋的顺风
北上。
我站在「海狼号」的甲板上,耳边是船帆的呼呼声与海盗们的喊号,目光却
不由自主地投向远方,心中既期待冒险,又隐隐不安。
航行数日,船上的生活逐渐显露出两派人的分野。
一种是宗教热情狂热的穆斯林,多为摩洛哥人和帝国雇佣兵,他们将此次远
征视为对异教徒的海上圣战。
每天清晨和黄昏,他们会在甲板上集体礼拜,齐声诵读《古兰经》,高喊
「真主至大」。
领头的是一名叙利亚来的毛拉,名叫艾哈迈德,瘦削而眼神炽热,总在布道
中宣扬掠夺基督教徒的财物是真主的旨意。
每当他挥舞手臂,船上的穆斯林便齐声应和,气氛热烈得仿佛要将海水点燃。
另一派人对宗教冷漠,眼中只有财富与荣誉。
他们多是改宗的欧洲叛逃者,荷兰人、英格兰人、西班牙人,因债务、冒险
或私仇背弃故土,皈依伊斯兰以求生存。
这些人聚在船头,喝酒、掷骰子,肆意嘲笑毛拉的布道。
他们谈论着冰岛的渔村如何富庶,传言那里的教堂藏有金银器皿,村民毫无
防备,只需一轮突袭便能满载而归,众人哄笑,却也掩不住眼中的贪婪。
我作为埃及掌旗官委任的帝国代表,每次礼拜,我都跪在甲板上,低头默念
经文,模仿他们的狂热。
但内心深处,我对这一切冷漠至极。
真主也好,财宝也罢,对我而言不过是活下去的手段。
船上的日子单调而艰苦。
白天,烈日炙烤甲板,海水反射的强光刺得人睁不开眼;夜晚,北大西洋的
寒风钻进骨头,连裹着羊毛毯也难抵寒意。
食物主要是硬面包、腌鱼和稀薄的麦粥,偶尔有从非洲海岸买来的干枣。
淡水严格配给,每人每天只有一小杯,舔舐杯底的咸味成了常态。
穆斯林与改宗者常因琐事争吵,饮水的分配、一句玩笑的冒犯,都可能引发
拳脚相向。
穆拉德冷眼旁观,只在冲突升级时才出面,用帝国委任状的权威或几句威胁
平息风波。
我注意到,那个挪威俘虏埃里克被单独关在底舱,只有导航时才被带上甲板。
他沉默寡言,但偶尔望向北方的眼神里,藏着复杂的情绪。
我试着用刚学的几句葡萄牙语与他交谈,他只冷冷回应:「冰岛的冰山比你
们想的硬。」
经过数周的颠簸航行,冰岛的轮廓终于出现在地平线上,北大西洋的寒风如
刀,切割着甲板上的每个人。
我站在「海狼号」的船头,眯眼望去,夏季的冰岛依然冷得刺骨。
海面上漂浮着零星的浮冰,远处的山巅覆盖着皑皑白雪,阳光虽明亮,却毫
无暖意。
穆斯林们挤在船舷边,指着浮冰和雪山惊呼不已,操着阿拉伯语和摩尔语议
论纷纷。
毛拉艾哈迈德高喊这是「真主创造的奇景」,却掩不住眼中的不安。
许多穆斯林从没见过冰雪,裹紧羊毛斗篷,宁愿缩在船舱里,也不愿冒险上
岸。
这景象难免让我想起以前听说过的高加索山脉的样子,只是这里比传说要更
加荒凉和寒冷,海岸边怪石嶙峋,山坡陡峭,不远处能看到正在喷涌的火山口和
流淌的熔岩,海岸边也不是黄色的海沙,而是黑色的火山灰和刺鼻的硫磺。
这水火交融的景象和附近的一切都仿佛在显示,这里是已知世界的尽头,再
向前一步就将不再有人类活动的痕迹。
改宗者们则表现迥异,那些来自荷兰、英格兰的叛兵,熟悉北欧的严寒,纷
纷嘲笑穆斯林的胆怯。
一个红发的大胆海盗脱下外套,赤裸上身站在船头,嚷道:「这点冷算什么?
波罗的海的冬天比这狠多了!」其他改宗者附和着,敲打刀剑,跃跃欲试。
穆拉德站在舵旁,冷眼扫视众人,下令准备登陆。
船队在冰岛东部的一个小海湾抛锚,海岸边散落着几座木屋,屋顶覆着草皮,
烟囱冒着微弱的炊烟。
穆拉德从挪威俘虏埃里克口中得知,这里的村庄名为贝拉加维克,是个以捕
鱼为生的小渔村,毫无防备。
果然如埃里克所言,冰岛人毫无防备。
村里只有几十户人家,男人多在海上捕鱼,留下的只有老弱妇孺。
他们见到我们时,先是愣住,随即尖叫着四散奔逃,毫无还手之力。
然而,村庄的贫瘠让海盗们大失所望。
木屋里只有粗糙的木桌、陶罐和几件破旧的羊毛衣物,教堂里连个像样的银
器都没有,只有一座木雕的十字架和几本破旧的经书。
海盗们咒骂道:「这鬼地方连个铜板都没有!」
穆拉德皱着眉,命令众人分散开来,搜刮一切能带走的东西,并尽可能抓捕
村民,准备带回萨利作为奴隶或勒索赎金。
穆拉德对我说:「这些北欧人虽穷,但在阿尔及尔的市场上,健康的白人奴
隶能卖个好价钱。」
我带队搜查村边的几间屋舍,手下的改宗者粗暴地砸门而入,将尖叫的妇人
和孩子拖到空地上。
穆斯林们大多留在船上,少数上岸的也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敷衍地翻找着破
烂。
我弯弓搭箭,警戒着周围,防止村民反抗,但内心却愈发冷漠。
这些冰岛人瘦弱而无助,眼神里满是恐惧,海盗们很快发现,冰岛的贫穷迫
使他们将目标转向人口。
突袭队分成几组,深入村落和附近的农舍,抓捕一切能走动的村民。
穆拉德也一脚踹开一间谷仓,拖出一个藏在干草里的少年,得意地用荷兰语
喊:「这小子能卖几十杜卡特!」
穆斯林们虽不情愿在寒冷中奔波,但在毛拉艾哈迈德的催促下,也加入了抓
捕,宣称这是「对异教徒的惩罚」。
我负责押送俘虏回海滩,沿途看着十几个村民被绳索捆绑,哭喊着被推搡前
行,其中一个老妇人摔倒在地,哀求着陌生的语言。
我冷着脸,挥手让手下拉她起来,心中却泛起一丝厌倦。
突袭并非毫无风险,几个年轻的冰岛男人从海上归来,见到村庄被袭,试图
用鱼叉、斧头、投石索反抗。
他们虽勇猛,却毫无章法,很快被海盗们的弯刀和火绳枪压制。
突袭持续了两天,海盗们抓捕了近四十名冰岛人,多为妇孺和少年,财物却
寥寥无几。
穆拉德下令继续航行,准备将俘虏带回萨利贩卖。
在冰岛海岸的数日突袭中,我们又袭击了几个沿海居民点,还有一座叫西人
岛的小岛和几座更小的岛屿。
但收获依然微薄,教堂空空荡荡,村民的木屋里只有破旧的渔网和腌鱼,连
像样的银器或皮毛都难寻。
一些不死心的叛教者海盗,尤其是来自日耳曼地区的,对俘虏的冰岛人进行
严厉的拷打和折磨,想要逼迫他们说出到底把钱藏在哪里了,可任凭如何毒打和
威胁,依然收获寥寥,看来这里的确是很难再榨出什么油水了。
最终,我们抓捕了约六百名冰岛人,塞满了三艘船的底舱。
这些人将成为我们这次远征的主要收入来源,弥补财物的匮乏。
随着船队远离冰岛,北大西洋的寒风稍缓,穆拉德下令对俘虏的管理稍作宽
松。
妇女和儿童被允许每日轮流到上层甲板放风,呼吸新鲜空气,缓解底舱的恶
臭与拥挤。
男性俘虏则被铁链锁住,分批带到甲板上,短暂活动筋骨。
穆拉德深知,这些渔民是此行的主要「财富」,必须保持他们的健康,才能
在萨利的奴隶市场上卖出好价钱。
他亲自巡视底舱,确保食物和淡水优先分配给俘虏,甚至下令严禁船员骚扰
女俘虏。
「谁敢碰女人,引发内讧,我就把他扔进海里喂鱼!」他在一次集会上咆哮
道,目光扫过穆斯林和改宗者,语气不容置疑。
这一命令暂时平息了船上的躁动。
穆斯林们忙于礼拜和看守俘虏,宣称这些「异教徒」将成为真主的仆役;改
宗者则聚在船头,掷骰子,计算着奴隶贩卖后的分成。
然而,船上的气氛依然紧绷。
几个改宗者私下抱怨,冰岛的贫瘠让他们的期望落空,有人甚至暗示,穆拉
德的领导或许不如传言中那么可靠。
尽管海盗头目们试图尽量缓和跟俘虏的关系,但是将要被恐怖异教徒奴役和
奸淫的前景,还是让十几个被抓来的未婚冰岛姑娘选择以绝食或跳海的方式自杀,
对此海盗们毫无办法,只能在晚上把她们的尸体抛入大海。
其他俘虏则多少认为这是上帝对他们信仰的考验,只要忍耐几年、十几年的
苦役生活,就有可能获得拯救,会被赎买回家。
在一次押送俘虏到甲板时,我注意到一个约二十岁的金发小妇人,名叫布林
娅,这是我从其他俘虏的低语中听来的。
她的美貌在人群中格外吸引我,即使她故意用尘土涂抹脸颊,试图掩盖自己
的吸引力。
她的蓝眼睛清澈而倔强,嘴唇紧抿,带着一丝挑衅的神情。
我看穿了她的伪装,心中泛起一股莫名的冲动。
这并非我第一次见到她,在冰岛打劫时,我推开房门走进一户人家,看到一
个年轻的母亲正在把自己的两个年幼的孩子藏到床底下,并让孩子们保持安静。
那个女人转身看到我破门而入,显得很慌张,伸手抓起旁边的草叉试图和我
拼命。
我在她扑过来时灵活地躲开,然后从后面把她绊倒,和两个闻声赶来的海盗
同伴一起把她压在地上,用绳子把她捆起来。
她很不安地看着我再次走进她的家里,我简单在里面搜索一下,没看到什么
值钱的东西,于是假装愤怒地用力把屋里的桌子和椅子等砸坏了堆在床前。
我想这样就不会再有人去检查床下了。
我走出那个女人的家门,对同伙说:「这里什么都没有,我们去教堂看看吧。」
我的海盗同伙也未作怀疑,等到把俘虏们聚拢到一起,驱赶他们上船时,那
个年轻的母亲四处张望,确定她的两个孩子没有被海盗抓来。
她有些感激地看了我一眼,然后低头被脱去外衣,只穿着单薄的内衣被搜身,
带上脚镣,关到船舱里,成为我们此行的战利品之一。
我试图接近她,我从自己的口粮中分出一些干枣和硬面包,趁押送她回底舱
时悄悄塞给她,期待换来一丝好感。
但她毫不领情,接过食物后立刻转手给了身旁的一个哭泣的孩子,头也不回
地瞪了我一眼。
那眼神既是挑衅,又带着不屑。
我愣在原地,心中却愈发着迷。
她的美貌和冷漠,点燃了我从未有过的执念。
尽管语言不通,她只会冰岛语,我只能用简单的葡萄牙语或刚学的荷兰语试
着交流,但我暗自下定决心:无论如何,我要得到她。
然而,我的行为并未逃过旁人的眼睛。
一名摩尔海盗警告我:「别忘了雷斯的命令。女人是整个团伙的财货,不是
你个人的玩物。」
我冷笑回应:「我只是给俘虏点吃的,免得她饿死卖不出价。」
我知道,船上的眼睛无处不在。
我必须小心行事,免得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返航的日子漫长而压抑。
船上食物和淡水日益紧张,俘虏的哭声与海盗的咒骂交织,空气中弥漫着不
安。
穆斯林们继续礼拜,毛拉艾哈迈德宣扬此行是真主的胜利,但连他也掩不住
对微薄收获的失望,改宗者们的抱怨越发公开。
一晚,布林娅再次被带到甲板放风。
我鼓起勇气,试图用葡萄牙语和她搭话,她转头,冷冷地看了我一眼,吐出
一串冰岛语,我一个字也听不懂。
但她的眼神明白无误:她恨我,恨我们所有人。
我退后一步,心中既挫败又着迷。
就在这时,挪威俘虏埃里克被带上甲板,他看了布林娅一眼,低声用蹩脚的
葡萄牙语对我说:「她不会对你低头的,冰岛人的性格都和那儿的冰山一样硬气。」
几个月后,舰队拖曳着疲惫的船帆驶入萨利港。
码头上照例挤满了人,可欢呼声稀稀拉拉。
穆拉德·雷斯站在「海狼号」艉楼,用尽力气才把场面稳住,高声宣布「战
果」:六百一十四名男女,外加几桶腌鱼、二十来张海豹皮。
人群一下子就从穆拉德宣布的战果里,看出了冰岛的穷困,立刻爆出一阵失
望的嘘声。
现在穆拉德急需现金来稳定部下人心,不然他马上就会遇到部下的叛乱,他
把这次抓来的俘虏,分成几份,卖给不同的奴隶贩子,有的当场结清,有的需要
一周内把钱付清,但这些钱显然还是不够,穆拉德被迫动用自己以前的积蓄,才
把给船员们的薪饷勉强凑够。
一周后,穆拉德正式给船员们分配这次的战利品份额,虽然所有人都大失所
望,可有总比没有好,大部分船员的怒火没有熄灭,只是暂时被推迟了。
比海盗船员的愤怒来得更快的,是穆拉德的这次远征投资人们的愤怒,穆拉
德只能以未来的成功暂时安抚他们。
趁着穆拉德因为这次远征亏损的机会,穆拉德的政敌们纷纷行动起来,萨利
共和国议会里的议员们决议解除穆拉德的公职,并威胁要把他赶出去。
穆拉德也只好决定过几天带着一些尚可信任的人,跟他乘坐一艘海盗船前往
阿尔及尔,投奔那里他认识的帕夏,继续海盗营生。
穆拉德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一起走,我表示同意,但是在那之前我要先去办一
件事,我刚打听到布林娅在哪个奴隶贩子手里,我要去把她买过来。
我在萨利的奴隶市场上找到了一个叫阿里的奴隶贩子,萨利的奴隶市场上大
多出售的都是黑奴,白人很少,白人女人更少,听说整个马格里布一年出售的白
人女奴往往只有几百个,有些年份只有十几个。
因此阿里的摊位格外显眼,我一眼就盯上了阿里正在出售的十几个奴隶里的
布林娅,但还是得装出挑挑拣拣的样子,免得奴隶贩子吃准了跟我坐地起价。
按这里标准,布林娅这样20多岁生过孩子的被分类为二等品,一等品是十几
岁的处女,只有帕夏和大贵族买得起,会被送入后宫里,以后的境遇全看自己的
本事。
20多岁的人妻是二等品,会成为普通家务女奴,往往会在劳累中过完凄惨的
一生。
在奴隶贩子的棍棒殴打下,布林娅被剥光了衣服,做几个深蹲,跑几步,走
几下,确认没有瘸腿之类的问题,我看到她这副羞耻的样子颇为心动,拽着布林
娅赤裸的身体左看右看,爱不释手,可还要上前指着她身上几处伤痕,假装不满
意地跟奴隶贩子砍价。
初步定下来后,几个犹太医生上前掰开布林娅的嘴,看看牙齿磨损推断是否
虚报年龄,通过给她一杯盐水,看看她漱口后吐出的水里是否有血丝等办法,检
查她身体有无明显疾病。
一番拉扯和争吵后,我把这次海盗分红的利润全拿了出来,才买下了布林娅,
毕竟市面上的白人女奴还是很少的。
付清了钱,我给布林娅在后腰上打上了标志她属于我的烙印,给她戴上一副
轻便的脚镣和手铐,把她装在麻袋里,扛进了穆拉德海盗船的货仓,途中布林娅
不时挣扎,我安抚几句,过几天就好了。
趁着涨潮的夜晚,穆拉德·雷斯离开了萨利海盗共和国,带走了不少叛教者
海盗和同样不受欢迎的至高帝国佣兵,穆拉德在船上说,他这么一走,萨利共和
国的摩洛哥派就会一家独大,恐怕过不了几年就会完全被摩洛哥吞并,结束短暂
的独立。
而我现在对萨利的命运毫不关心,只想到了阿尔及尔有时间休息一段时间,
享受一下到目前唯一的收获。
在阿尔及尔能俯看港湾的山坡上,穆拉德给我给我找了一个带水井的小院,
里面有一间石头砌筑的房子,整体不大,但两个人住还很宽松,他告诉我他和其
他海盗就住在附近,无必要不要离开阿尔及尔城区,城外常有图阿雷格人的土匪
出没,他们会随意洗劫任何遇到的人,一定要出城就要跟随武装商团一起结伴而
行才安全。
我把布林娅关在我的房子里,把她清洗干净,让布林娅带着脚镣做家务,告
诉她,我打听过了,冰岛派来赎人的老牧师带来的钱只够赎回5 个人的,其中没
有她,她的两个孩子被他的丈夫继续抚养,可她丈夫听话她死了,已经和别的女
人结婚了。
布林娅听后稍微安心,却并不全信,她认为他丈夫不会这么快就另觅新欢,
但相隔这么远消息不同,她也毫无办法。
晚上我让布林娅给我侍寝,她拒绝,我打了她几下,把布林娅的双手用粗麻
绳紧紧捆在身后,绳结勒进她白皙的皮肤里,她的身体还在微微颤抖,那双蓝眼
睛里满是愤怒和恐惧,却没有一丝求饶的意思。
阿尔及尔的夜风从窗户缝隙吹进来,带着海港的咸腥味,我盯着她那丰满的
胸脯随着呼吸起伏,成熟的身躯像熟透的果实,随便一碰就能挤出汁水来。
我一把将她推倒在简陋的床上,那床铺是用稻草和旧布堆成的,她摔下去时
发出一声闷哼,赤裸的身体在烛光下泛着光泽。
「你这个异教徒的畜生!」
布林娅用生硬的摩尔语骂道,她从奴隶贩子那里学了些零碎的词句,现在全
用来宣泄恨意,「放开我,你以为这样就能让我屈服?」
我大笑起来,声音在石头墙壁间回荡,「屈服?宝贝,我才不管你服不服。
你现在是我的财产,身体是我的玩具。」
我跪在她身边,一只手粗鲁地抓住她的奶子,用力捏揉,那丰满的乳肉从指
缝溢出,她的身体立刻有了反应,乳头硬挺起来,下面那骚逼隐隐渗出湿意。
但她的眼神呆滞,像死鱼一样,没有任何迎合,只是顺从地躺着,任我摆弄。
我脱掉自己的袍子,露出早已硬邦邦的鸡巴,粗长的家伙直挺挺地对着她。
我分开她的双腿,她没反抗,只是转过头去,咬着嘴唇。
我用手指探进她的骚逼,里面已经湿润了,随便撩拨几下,她的身体就抽搐
起来,汁水顺着大腿流下。
「看吧,你的身体比你的嘴诚实多了,」
我嘲笑道,「它知道谁是主人。」
她喘息着,声音带着颤抖,「上帝会惩罚你的……你这个撒旦的走狗。」
我没理她,直接挺腰插进去,那紧致的骚逼包裹着我的鸡巴,像吸吮一样吞
没了我。
我开始猛烈抽插,每一下都顶到最深,她的身体随着我的节奏摇晃,奶子晃
荡着,发出啪啪的肉体撞击声。
但她没叫床,没迎合,只是目光空洞地盯着天花板,像个木偶。
我越操越起劲,双手掐着她的腰,汗水滴在她身上,她终于忍不住,低声咒
骂,「畜生……去死吧。」
我加快速度,鸡巴在她的体内搅动,感觉她的子宫在收缩,终于一股热流涌
出,我满意地灌满了她的里面,白浆从结合处溢出,顺着她的屁股流到床上。
我拔出来时,她的身体还在痉挛,但眼神依旧冷漠,没有一丝快感。
第二天早上,阳光洒进小院子,我懒洋洋地躺在床上,看着布林娅半裸着身
体,带着脚镣在房间里做家务。
脚镣的链子叮当作响,每走一步都提醒她自己的身份。
她弯腰擦地板时,那丰满的屁股翘起,骚逼和屁眼暴露无遗,后腰上还有她
奴隶身份的烙铁印。
我忍不住走过去,从身后抱住她,一只手伸到前面揉她的奶子,另一只手探
进她的腿间。
「别……停下,」她低声说,但身体已经软了,随便撩拨几下,下面就湿了。
我哈哈大笑,「停下?这是你的日常工作,骚货。」我手指插进她的骚逼,
搅动着,汁水溅出,她咬牙忍着,没迎合,但也没反抗。
我玩够了,就让她继续干活,不时走过去骚扰她一下,撩起裙子捏捏屁股,
舔舔奶头,看着她强忍的模样,心里满足极了。
我允许她按照她的基督教信仰做祷告,毕竟这能让她觉得活着还有点希望。
下午,她跪在墙角,双手合十,低声念着经文,那双蓝眼睛闭着,脸上是难
得的平静。
但我走过去,蹲在她身边,笑着说,「祈祷吧,宝贝。上帝能救你吗?」
她睁开眼,声音平静却带着绝望,我知道自己注定得不到她的心,但她的身
体已经完全归我所有。
我可以肆意奸淫玩弄她,每天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监视下。
她洗澡时我看着,她睡觉时我抱着,她甚至上厕所我都守在旁边。
起初她还会反抗,骂我,但渐渐地,被绝望感侵蚀的布林娅变得驯服,像只
被驯化的母狗。
但我清楚,这不是真心服从,她只是无处可逃。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逐渐不满足于简单的强奸。
那天,我从市场上买来灌肠用具,专门用来清洁肠道的,晚上我把布林娅按
在床上,四肢绑紧,她挣扎着,「你要干什么?别碰我那里!」
「闭嘴,贱货,」我冷笑,「今天玩玩你的屁眼。」
我把管子插进她的屁眼,注入温水和油,慢慢排空她的肠道。
她痛苦地扭动,脸红得像煮熟的虾,「啊……疼……你这个变态!」
排空后,她的屁眼干净光滑,褐色的小洞看起来很是诱人,我在她的屁眼上
抹上油,鸡巴对准那紧致的洞口,缓缓推进。
她尖叫起来,「不!停下!那里不是……啊!」
但她的身体顺从地张开,我开始抽插,鸡巴在她的屁眼里进出,感觉比骚逼
还紧致。
「操!你的屁眼真他妈会夹!」我吼道,一只手打她的屁股,啪啪作响。
她哭喊着,「撒旦的仆人!你会下地狱的!」
我越操越猛,最后射在她里面,白浆从屁眼溢出。
她瘫软下来,目光呆滞,但身体还在抽搐。
从那天起,我更变本加厉。
有一天,我把她按在我的大腿上,像打孩子一样,用手掌打她的屁股。
她的屁股丰满,弹性十足,每一巴掌下去都留下红印,她扭动着,「停下!
疼……你这个畜生!」
「疼?这是奖励,母狗,」
我大笑,「你不乖,我就打到你求饶。」
我打了几十下,她的屁股红肿,下面却湿透了。
我手指插进去搅动,她喘息着,「别……我恨你。」
但她的身体反应诚实,我满意地又操了她一顿。
我还试了更刺激的玩法。
把她双腿分开的倒着吊起来,用绳子绑在天花板的钩子上,她头朝下,奶子
垂着,骚逼大开。
我在她的骚逼里插上鲜花,一朵朵红色的野花塞进去,露出一截花茎,她羞
耻地哭喊,「拿出来!你这个疯子!这是亵渎!」
「亵渎?你的骚逼就是我的花园,」
我嘲笑,另一天换成蜡烛,点燃后插进去,蜡油滴在她里面,她尖叫,「烫!
啊……烧起来了!」
我看着她痛苦的样子,鸡巴硬了,直接操她的嘴,射在她喉咙里。
为了让她永远记住,我在大腿正面也烙印标记,一个我的符号,烫在她白嫩
的皮肤上。
每次她祈祷,跪下时就能看见那烙印。
她咒骂我是撒旦的仆人,我奖励她的子宫又一次被我的白浆灌满。
「骂吧,臭婊子,」
我边操边说,「你的子宫爱我的精液,它会吞下每一滴。」
布林娅逐渐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她不再大吵大闹,变得乖巧,但眼神里总有
那抹绝望。
我知道她只是无处可逃,而被迫适应和我在一起。
白天,我看着她拖着脚镣扫地,奶子晃荡,屁股扭动,不时走过去骚扰她,
捏她的奶头,拉她的骚逼唇,她顺从地张开腿,任我手指玩弄。
「主人……要操我吗?」她有时会低声问,但声音空洞,没有情感。
「对,骚货,」我把她按在桌子上,从后面插进去,鸡巴撞击她的屁股,啪
啪作响,「你的身体是我的,永远是!」
她喘息着,「是的……主人。」
但她的心,我知道,永远遥远。
日子就这样继续,我在阿尔及尔的小院子里,享受着这个金发奴隶带来的乐
趣。
有一天晚上,我又把她绑起来,玩她的屁眼,灌肠后直接操,她哭喊着,
「够了……我受不了了!」
「受不了?那就求我,」我吼道,鸡巴猛插。
她终于低声说,「求你……操我吧,主人。」
但她的眼神依旧呆滞,没有真心。
我射在她里面,满意地抱着她睡去,早上我看着她还没醒来的样子,觉得她
可爱极了,在她脸上亲了好一会儿,搂着她温暖丰满的身体,一种幸福满充满全
身。
白天时,我让她对我笑一下,布林娅依然冷着脸,尽量克制的对我说:「你
毁了我的家,却以为我会爱你吗?我的心永远不会属于你。」
【第一章·完】
2025/09/02发表于:SIS001
是否首发:是
字数:10,993 字
第一章
今年,按法兰克人的算法是1626年,按我们的迁徙历算,则是1035年。
我这天正好有空,走进了埃及亚历山大港一座我常去的咖啡馆。
店主向我介绍了一个看起来是红头发的中年人,他自称穆拉德·雷斯,原名
杨·杨松,以前是个荷兰的海盗船长,后来荷兰与西班牙议和后,他转投摩洛哥
海岸的萨利海盗共和国,并在那里颇有威望,但最近几年萨利共和国内讧不断,
他打算到埃及来通过贿赂获得至高帝国的正式委任,以强化自身地位,靠帝国权
威压制内部政敌。
他向咖啡厅店主打听后,得知我正好在给亚历山大港的至高帝国海军掌旗官
做卫兵,由于我这几年来多次参加埃及舰队与基督徒海盗的作战,屡次和同伴击
退了海盗发起的跳帮作战,保护了掌旗官的安全,因此颇受信任,正好适合引荐
给亚历山大港的帝国海军掌旗官。
杨松还和我说起,他通过俘虏的一个挪威船员,得知了冰岛因为地处偏远而
疏于防备,希望明年夏天发起的这次冰岛远征能为他建立威名,进一步强化他在
萨利共和国的地位。
杨松这番话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我出身鲁梅里亚的西帕西领主家族,是
家中第五个儿子,注定无法继承家业,在接受了家族能提供的多年军事训练后,
带着一张弓和一匹骡子外出闯荡,和我同行的几个伙伴自嘲:「像我们这种提马
尔家的小儿子,只能给耶尼切里扛旗」,但现在帝国与各方敌人的摩擦不断,从
军和发财的机会还是不少的。
我想起姐姐法蒂玛跟随一船的人,从萨洛尼卡乘船去亚历山大港,要去红海
边的两圣地朝圣时,遭遇了异教徒海盗的袭击,那是一伙自称医院骑士团的海盗,
听说他们把我姐姐贴上了土耳其女人的标签,卖到了意大利为奴,从此我再也没
见过她。
于是我下定决心加入了帝国海军的埃及舰队,希望能打探到姐姐的下落。
我到亚历山大后,船上的熟人介绍我把骡子卖给一个希腊人老铁匠,他给了
我一柄二手波斯弯刀,刀面磨掉了前主人的名字,只留一行「愿真主恩赐胜利」。
我从普通的船上弓箭手做起,五六年来历经大小十余次战斗,树立了自己的
些许名声,被掌旗官选中做他的侍从。
回想往事,我在埃及生活的这几年,虽然收到了不少赏赐,生活富裕,但难
免觉得十分孤独,并被本地人多有排斥,当地埃及人把我视为从北方来的鲁姆人,
常把对帝国征税的不满转化成对我的冷眼相待。
因此我也希望能通过新的冒险填补心理的空虚。
于是同意了为杨松引荐,并希望加入他的海盗团。
记得刚来埃及时我还曾请求掌旗官的书记官,替我查过马耳他来的俘虏名册,
几年前确有一名叫法蒂玛·阿普杜拉的女俘虏,年龄籍贯都对得上,后面写着她
在拿坡里被转卖了。
我想若不能救回姐姐,便让十字架下的女人也尝尝被锁链拖过甲板的滋味。
杨松船长向哈立德掌旗官送上劫掠来的数千金币和其他财物,掌旗官十分满
意,当即表示他会马上向帝国高门推荐杨松船长担任帝国的正式雷斯,委任状很
快就能准备好。
杨松进一步提出,能带几个人回去做帝国的代表更好,掌旗官会意地派了我
等几个人一起去,临行时对我们说:「等以后回来了,别忘了分享一下你们的冒
险故事,这值得帝国臣民为之传颂。」
离开亚历山大港后,我随穆拉德·雷斯乘船西行,沿马格里布海岸航行数周,
终于在1626年秋抵达摩洛哥的萨利海盗共和国。
海风夹杂着盐腥与港口的喧嚣扑面而来,萨利的景象既熟悉又陌生,这是一
座由海盗、叛军与冒险者共筑的混乱之城,表面繁荣,内里暗流涌动。
我立刻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紧张气氛,穆拉德·雷斯告诉我,萨利现在分裂为
两派:一派是忠于他的新海盗,多为荷兰、英格兰等欧洲国家的叛逃者,主张与
帝国保持松散联系以换取更大自由;另一派是本地摩洛哥人和从西班牙被驱逐的
摩尔人,主张就近依附摩洛哥王国以获取保护,两派互相争抢战利品分配和海盗
舰队的主导权。
穆拉德带我走进一间由旧堡垒改建的萨利城邦议会,二十余名海盗头目和当
地贵族围坐一圈,争吵不休,一名摩尔人拍桌怒吼:「你的冰岛远征是妄想,只
会浪费勇士的鲜血和我们宝贵的战船!」
穆拉德冷笑,掏出奥斯曼掌旗官的委任状,宣布自己已被帝国正式任命为帝
国海军的雷斯,承诺将战利品公平分配,并以帝国权威震慑反对者。
厅内短暂沉默,但我注意到几人眼中仍闪过不信任的光芒。
穆拉德私下对我说:「这张纸只能压住他们一时,冰岛远征必须成功,否则
我在这里很难立足。」
接下来的日子,萨利的港口忙碌异常,穆拉德的海盗团为冰岛远征做最后准
备。
他的舰队包括三艘主力船:旗舰「海狼号」,一艘改装自荷兰商船的快速帆
船,配备12门火炮;以及两艘较小的单桅船,适合近岸突袭。
船上那些炮手多是欧洲叛教者,言辞粗鲁但技术过硬。
穆拉德为远征召集了200 多名海盗,混合了摩洛哥人、欧洲叛逃者和少量帝
国雇佣兵。
他们聚集在港口附近的沙滩上操练,练习跳帮作战。
一天夜深人静,穆拉德召集众人,宣布远征将在来年夏初启航,目标是冰岛
的丰饶渔村与无防备的港口,冰岛以前从未被帝国海军所触及过,这次探险的范
围远超过以前帝国海军的活动范围,仅凭这点,能参加这次远征,就是前所未有
的壮举,为帝国海军增添了新的荣誉,我们必将因此而名扬天下,为后世传颂。
海盗们举起弯刀,高喊着真主的荣光与财宝的诱惑。
1627年夏初,萨利的港口烈日炙烤,穆拉德·雷斯的舰队终于扬帆起航,目
标直指冰岛。
三艘船,旗舰「海狼号」和两艘单桅船载着百余名海盗,乘着大西洋的顺风
北上。
我站在「海狼号」的甲板上,耳边是船帆的呼呼声与海盗们的喊号,目光却
不由自主地投向远方,心中既期待冒险,又隐隐不安。
航行数日,船上的生活逐渐显露出两派人的分野。
一种是宗教热情狂热的穆斯林,多为摩洛哥人和帝国雇佣兵,他们将此次远
征视为对异教徒的海上圣战。
每天清晨和黄昏,他们会在甲板上集体礼拜,齐声诵读《古兰经》,高喊
「真主至大」。
领头的是一名叙利亚来的毛拉,名叫艾哈迈德,瘦削而眼神炽热,总在布道
中宣扬掠夺基督教徒的财物是真主的旨意。
每当他挥舞手臂,船上的穆斯林便齐声应和,气氛热烈得仿佛要将海水点燃。
另一派人对宗教冷漠,眼中只有财富与荣誉。
他们多是改宗的欧洲叛逃者,荷兰人、英格兰人、西班牙人,因债务、冒险
或私仇背弃故土,皈依伊斯兰以求生存。
这些人聚在船头,喝酒、掷骰子,肆意嘲笑毛拉的布道。
他们谈论着冰岛的渔村如何富庶,传言那里的教堂藏有金银器皿,村民毫无
防备,只需一轮突袭便能满载而归,众人哄笑,却也掩不住眼中的贪婪。
我作为埃及掌旗官委任的帝国代表,每次礼拜,我都跪在甲板上,低头默念
经文,模仿他们的狂热。
但内心深处,我对这一切冷漠至极。
真主也好,财宝也罢,对我而言不过是活下去的手段。
船上的日子单调而艰苦。
白天,烈日炙烤甲板,海水反射的强光刺得人睁不开眼;夜晚,北大西洋的
寒风钻进骨头,连裹着羊毛毯也难抵寒意。
食物主要是硬面包、腌鱼和稀薄的麦粥,偶尔有从非洲海岸买来的干枣。
淡水严格配给,每人每天只有一小杯,舔舐杯底的咸味成了常态。
穆斯林与改宗者常因琐事争吵,饮水的分配、一句玩笑的冒犯,都可能引发
拳脚相向。
穆拉德冷眼旁观,只在冲突升级时才出面,用帝国委任状的权威或几句威胁
平息风波。
我注意到,那个挪威俘虏埃里克被单独关在底舱,只有导航时才被带上甲板。
他沉默寡言,但偶尔望向北方的眼神里,藏着复杂的情绪。
我试着用刚学的几句葡萄牙语与他交谈,他只冷冷回应:「冰岛的冰山比你
们想的硬。」
经过数周的颠簸航行,冰岛的轮廓终于出现在地平线上,北大西洋的寒风如
刀,切割着甲板上的每个人。
我站在「海狼号」的船头,眯眼望去,夏季的冰岛依然冷得刺骨。
海面上漂浮着零星的浮冰,远处的山巅覆盖着皑皑白雪,阳光虽明亮,却毫
无暖意。
穆斯林们挤在船舷边,指着浮冰和雪山惊呼不已,操着阿拉伯语和摩尔语议
论纷纷。
毛拉艾哈迈德高喊这是「真主创造的奇景」,却掩不住眼中的不安。
许多穆斯林从没见过冰雪,裹紧羊毛斗篷,宁愿缩在船舱里,也不愿冒险上
岸。
这景象难免让我想起以前听说过的高加索山脉的样子,只是这里比传说要更
加荒凉和寒冷,海岸边怪石嶙峋,山坡陡峭,不远处能看到正在喷涌的火山口和
流淌的熔岩,海岸边也不是黄色的海沙,而是黑色的火山灰和刺鼻的硫磺。
这水火交融的景象和附近的一切都仿佛在显示,这里是已知世界的尽头,再
向前一步就将不再有人类活动的痕迹。
改宗者们则表现迥异,那些来自荷兰、英格兰的叛兵,熟悉北欧的严寒,纷
纷嘲笑穆斯林的胆怯。
一个红发的大胆海盗脱下外套,赤裸上身站在船头,嚷道:「这点冷算什么?
波罗的海的冬天比这狠多了!」其他改宗者附和着,敲打刀剑,跃跃欲试。
穆拉德站在舵旁,冷眼扫视众人,下令准备登陆。
船队在冰岛东部的一个小海湾抛锚,海岸边散落着几座木屋,屋顶覆着草皮,
烟囱冒着微弱的炊烟。
穆拉德从挪威俘虏埃里克口中得知,这里的村庄名为贝拉加维克,是个以捕
鱼为生的小渔村,毫无防备。
果然如埃里克所言,冰岛人毫无防备。
村里只有几十户人家,男人多在海上捕鱼,留下的只有老弱妇孺。
他们见到我们时,先是愣住,随即尖叫着四散奔逃,毫无还手之力。
然而,村庄的贫瘠让海盗们大失所望。
木屋里只有粗糙的木桌、陶罐和几件破旧的羊毛衣物,教堂里连个像样的银
器都没有,只有一座木雕的十字架和几本破旧的经书。
海盗们咒骂道:「这鬼地方连个铜板都没有!」
穆拉德皱着眉,命令众人分散开来,搜刮一切能带走的东西,并尽可能抓捕
村民,准备带回萨利作为奴隶或勒索赎金。
穆拉德对我说:「这些北欧人虽穷,但在阿尔及尔的市场上,健康的白人奴
隶能卖个好价钱。」
我带队搜查村边的几间屋舍,手下的改宗者粗暴地砸门而入,将尖叫的妇人
和孩子拖到空地上。
穆斯林们大多留在船上,少数上岸的也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敷衍地翻找着破
烂。
我弯弓搭箭,警戒着周围,防止村民反抗,但内心却愈发冷漠。
这些冰岛人瘦弱而无助,眼神里满是恐惧,海盗们很快发现,冰岛的贫穷迫
使他们将目标转向人口。
突袭队分成几组,深入村落和附近的农舍,抓捕一切能走动的村民。
穆拉德也一脚踹开一间谷仓,拖出一个藏在干草里的少年,得意地用荷兰语
喊:「这小子能卖几十杜卡特!」
穆斯林们虽不情愿在寒冷中奔波,但在毛拉艾哈迈德的催促下,也加入了抓
捕,宣称这是「对异教徒的惩罚」。
我负责押送俘虏回海滩,沿途看着十几个村民被绳索捆绑,哭喊着被推搡前
行,其中一个老妇人摔倒在地,哀求着陌生的语言。
我冷着脸,挥手让手下拉她起来,心中却泛起一丝厌倦。
突袭并非毫无风险,几个年轻的冰岛男人从海上归来,见到村庄被袭,试图
用鱼叉、斧头、投石索反抗。
他们虽勇猛,却毫无章法,很快被海盗们的弯刀和火绳枪压制。
突袭持续了两天,海盗们抓捕了近四十名冰岛人,多为妇孺和少年,财物却
寥寥无几。
穆拉德下令继续航行,准备将俘虏带回萨利贩卖。
在冰岛海岸的数日突袭中,我们又袭击了几个沿海居民点,还有一座叫西人
岛的小岛和几座更小的岛屿。
但收获依然微薄,教堂空空荡荡,村民的木屋里只有破旧的渔网和腌鱼,连
像样的银器或皮毛都难寻。
一些不死心的叛教者海盗,尤其是来自日耳曼地区的,对俘虏的冰岛人进行
严厉的拷打和折磨,想要逼迫他们说出到底把钱藏在哪里了,可任凭如何毒打和
威胁,依然收获寥寥,看来这里的确是很难再榨出什么油水了。
最终,我们抓捕了约六百名冰岛人,塞满了三艘船的底舱。
这些人将成为我们这次远征的主要收入来源,弥补财物的匮乏。
随着船队远离冰岛,北大西洋的寒风稍缓,穆拉德下令对俘虏的管理稍作宽
松。
妇女和儿童被允许每日轮流到上层甲板放风,呼吸新鲜空气,缓解底舱的恶
臭与拥挤。
男性俘虏则被铁链锁住,分批带到甲板上,短暂活动筋骨。
穆拉德深知,这些渔民是此行的主要「财富」,必须保持他们的健康,才能
在萨利的奴隶市场上卖出好价钱。
他亲自巡视底舱,确保食物和淡水优先分配给俘虏,甚至下令严禁船员骚扰
女俘虏。
「谁敢碰女人,引发内讧,我就把他扔进海里喂鱼!」他在一次集会上咆哮
道,目光扫过穆斯林和改宗者,语气不容置疑。
这一命令暂时平息了船上的躁动。
穆斯林们忙于礼拜和看守俘虏,宣称这些「异教徒」将成为真主的仆役;改
宗者则聚在船头,掷骰子,计算着奴隶贩卖后的分成。
然而,船上的气氛依然紧绷。
几个改宗者私下抱怨,冰岛的贫瘠让他们的期望落空,有人甚至暗示,穆拉
德的领导或许不如传言中那么可靠。
尽管海盗头目们试图尽量缓和跟俘虏的关系,但是将要被恐怖异教徒奴役和
奸淫的前景,还是让十几个被抓来的未婚冰岛姑娘选择以绝食或跳海的方式自杀,
对此海盗们毫无办法,只能在晚上把她们的尸体抛入大海。
其他俘虏则多少认为这是上帝对他们信仰的考验,只要忍耐几年、十几年的
苦役生活,就有可能获得拯救,会被赎买回家。
在一次押送俘虏到甲板时,我注意到一个约二十岁的金发小妇人,名叫布林
娅,这是我从其他俘虏的低语中听来的。
她的美貌在人群中格外吸引我,即使她故意用尘土涂抹脸颊,试图掩盖自己
的吸引力。
她的蓝眼睛清澈而倔强,嘴唇紧抿,带着一丝挑衅的神情。
我看穿了她的伪装,心中泛起一股莫名的冲动。
这并非我第一次见到她,在冰岛打劫时,我推开房门走进一户人家,看到一
个年轻的母亲正在把自己的两个年幼的孩子藏到床底下,并让孩子们保持安静。
那个女人转身看到我破门而入,显得很慌张,伸手抓起旁边的草叉试图和我
拼命。
我在她扑过来时灵活地躲开,然后从后面把她绊倒,和两个闻声赶来的海盗
同伴一起把她压在地上,用绳子把她捆起来。
她很不安地看着我再次走进她的家里,我简单在里面搜索一下,没看到什么
值钱的东西,于是假装愤怒地用力把屋里的桌子和椅子等砸坏了堆在床前。
我想这样就不会再有人去检查床下了。
我走出那个女人的家门,对同伙说:「这里什么都没有,我们去教堂看看吧。」
我的海盗同伙也未作怀疑,等到把俘虏们聚拢到一起,驱赶他们上船时,那
个年轻的母亲四处张望,确定她的两个孩子没有被海盗抓来。
她有些感激地看了我一眼,然后低头被脱去外衣,只穿着单薄的内衣被搜身,
带上脚镣,关到船舱里,成为我们此行的战利品之一。
我试图接近她,我从自己的口粮中分出一些干枣和硬面包,趁押送她回底舱
时悄悄塞给她,期待换来一丝好感。
但她毫不领情,接过食物后立刻转手给了身旁的一个哭泣的孩子,头也不回
地瞪了我一眼。
那眼神既是挑衅,又带着不屑。
我愣在原地,心中却愈发着迷。
她的美貌和冷漠,点燃了我从未有过的执念。
尽管语言不通,她只会冰岛语,我只能用简单的葡萄牙语或刚学的荷兰语试
着交流,但我暗自下定决心:无论如何,我要得到她。
然而,我的行为并未逃过旁人的眼睛。
一名摩尔海盗警告我:「别忘了雷斯的命令。女人是整个团伙的财货,不是
你个人的玩物。」
我冷笑回应:「我只是给俘虏点吃的,免得她饿死卖不出价。」
我知道,船上的眼睛无处不在。
我必须小心行事,免得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返航的日子漫长而压抑。
船上食物和淡水日益紧张,俘虏的哭声与海盗的咒骂交织,空气中弥漫着不
安。
穆斯林们继续礼拜,毛拉艾哈迈德宣扬此行是真主的胜利,但连他也掩不住
对微薄收获的失望,改宗者们的抱怨越发公开。
一晚,布林娅再次被带到甲板放风。
我鼓起勇气,试图用葡萄牙语和她搭话,她转头,冷冷地看了我一眼,吐出
一串冰岛语,我一个字也听不懂。
但她的眼神明白无误:她恨我,恨我们所有人。
我退后一步,心中既挫败又着迷。
就在这时,挪威俘虏埃里克被带上甲板,他看了布林娅一眼,低声用蹩脚的
葡萄牙语对我说:「她不会对你低头的,冰岛人的性格都和那儿的冰山一样硬气。」
几个月后,舰队拖曳着疲惫的船帆驶入萨利港。
码头上照例挤满了人,可欢呼声稀稀拉拉。
穆拉德·雷斯站在「海狼号」艉楼,用尽力气才把场面稳住,高声宣布「战
果」:六百一十四名男女,外加几桶腌鱼、二十来张海豹皮。
人群一下子就从穆拉德宣布的战果里,看出了冰岛的穷困,立刻爆出一阵失
望的嘘声。
现在穆拉德急需现金来稳定部下人心,不然他马上就会遇到部下的叛乱,他
把这次抓来的俘虏,分成几份,卖给不同的奴隶贩子,有的当场结清,有的需要
一周内把钱付清,但这些钱显然还是不够,穆拉德被迫动用自己以前的积蓄,才
把给船员们的薪饷勉强凑够。
一周后,穆拉德正式给船员们分配这次的战利品份额,虽然所有人都大失所
望,可有总比没有好,大部分船员的怒火没有熄灭,只是暂时被推迟了。
比海盗船员的愤怒来得更快的,是穆拉德的这次远征投资人们的愤怒,穆拉
德只能以未来的成功暂时安抚他们。
趁着穆拉德因为这次远征亏损的机会,穆拉德的政敌们纷纷行动起来,萨利
共和国议会里的议员们决议解除穆拉德的公职,并威胁要把他赶出去。
穆拉德也只好决定过几天带着一些尚可信任的人,跟他乘坐一艘海盗船前往
阿尔及尔,投奔那里他认识的帕夏,继续海盗营生。
穆拉德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一起走,我表示同意,但是在那之前我要先去办一
件事,我刚打听到布林娅在哪个奴隶贩子手里,我要去把她买过来。
我在萨利的奴隶市场上找到了一个叫阿里的奴隶贩子,萨利的奴隶市场上大
多出售的都是黑奴,白人很少,白人女人更少,听说整个马格里布一年出售的白
人女奴往往只有几百个,有些年份只有十几个。
因此阿里的摊位格外显眼,我一眼就盯上了阿里正在出售的十几个奴隶里的
布林娅,但还是得装出挑挑拣拣的样子,免得奴隶贩子吃准了跟我坐地起价。
按这里标准,布林娅这样20多岁生过孩子的被分类为二等品,一等品是十几
岁的处女,只有帕夏和大贵族买得起,会被送入后宫里,以后的境遇全看自己的
本事。
20多岁的人妻是二等品,会成为普通家务女奴,往往会在劳累中过完凄惨的
一生。
在奴隶贩子的棍棒殴打下,布林娅被剥光了衣服,做几个深蹲,跑几步,走
几下,确认没有瘸腿之类的问题,我看到她这副羞耻的样子颇为心动,拽着布林
娅赤裸的身体左看右看,爱不释手,可还要上前指着她身上几处伤痕,假装不满
意地跟奴隶贩子砍价。
初步定下来后,几个犹太医生上前掰开布林娅的嘴,看看牙齿磨损推断是否
虚报年龄,通过给她一杯盐水,看看她漱口后吐出的水里是否有血丝等办法,检
查她身体有无明显疾病。
一番拉扯和争吵后,我把这次海盗分红的利润全拿了出来,才买下了布林娅,
毕竟市面上的白人女奴还是很少的。
付清了钱,我给布林娅在后腰上打上了标志她属于我的烙印,给她戴上一副
轻便的脚镣和手铐,把她装在麻袋里,扛进了穆拉德海盗船的货仓,途中布林娅
不时挣扎,我安抚几句,过几天就好了。
趁着涨潮的夜晚,穆拉德·雷斯离开了萨利海盗共和国,带走了不少叛教者
海盗和同样不受欢迎的至高帝国佣兵,穆拉德在船上说,他这么一走,萨利共和
国的摩洛哥派就会一家独大,恐怕过不了几年就会完全被摩洛哥吞并,结束短暂
的独立。
而我现在对萨利的命运毫不关心,只想到了阿尔及尔有时间休息一段时间,
享受一下到目前唯一的收获。
在阿尔及尔能俯看港湾的山坡上,穆拉德给我给我找了一个带水井的小院,
里面有一间石头砌筑的房子,整体不大,但两个人住还很宽松,他告诉我他和其
他海盗就住在附近,无必要不要离开阿尔及尔城区,城外常有图阿雷格人的土匪
出没,他们会随意洗劫任何遇到的人,一定要出城就要跟随武装商团一起结伴而
行才安全。
我把布林娅关在我的房子里,把她清洗干净,让布林娅带着脚镣做家务,告
诉她,我打听过了,冰岛派来赎人的老牧师带来的钱只够赎回5 个人的,其中没
有她,她的两个孩子被他的丈夫继续抚养,可她丈夫听话她死了,已经和别的女
人结婚了。
布林娅听后稍微安心,却并不全信,她认为他丈夫不会这么快就另觅新欢,
但相隔这么远消息不同,她也毫无办法。
晚上我让布林娅给我侍寝,她拒绝,我打了她几下,把布林娅的双手用粗麻
绳紧紧捆在身后,绳结勒进她白皙的皮肤里,她的身体还在微微颤抖,那双蓝眼
睛里满是愤怒和恐惧,却没有一丝求饶的意思。
阿尔及尔的夜风从窗户缝隙吹进来,带着海港的咸腥味,我盯着她那丰满的
胸脯随着呼吸起伏,成熟的身躯像熟透的果实,随便一碰就能挤出汁水来。
我一把将她推倒在简陋的床上,那床铺是用稻草和旧布堆成的,她摔下去时
发出一声闷哼,赤裸的身体在烛光下泛着光泽。
「你这个异教徒的畜生!」
布林娅用生硬的摩尔语骂道,她从奴隶贩子那里学了些零碎的词句,现在全
用来宣泄恨意,「放开我,你以为这样就能让我屈服?」
我大笑起来,声音在石头墙壁间回荡,「屈服?宝贝,我才不管你服不服。
你现在是我的财产,身体是我的玩具。」
我跪在她身边,一只手粗鲁地抓住她的奶子,用力捏揉,那丰满的乳肉从指
缝溢出,她的身体立刻有了反应,乳头硬挺起来,下面那骚逼隐隐渗出湿意。
但她的眼神呆滞,像死鱼一样,没有任何迎合,只是顺从地躺着,任我摆弄。
我脱掉自己的袍子,露出早已硬邦邦的鸡巴,粗长的家伙直挺挺地对着她。
我分开她的双腿,她没反抗,只是转过头去,咬着嘴唇。
我用手指探进她的骚逼,里面已经湿润了,随便撩拨几下,她的身体就抽搐
起来,汁水顺着大腿流下。
「看吧,你的身体比你的嘴诚实多了,」
我嘲笑道,「它知道谁是主人。」
她喘息着,声音带着颤抖,「上帝会惩罚你的……你这个撒旦的走狗。」
我没理她,直接挺腰插进去,那紧致的骚逼包裹着我的鸡巴,像吸吮一样吞
没了我。
我开始猛烈抽插,每一下都顶到最深,她的身体随着我的节奏摇晃,奶子晃
荡着,发出啪啪的肉体撞击声。
但她没叫床,没迎合,只是目光空洞地盯着天花板,像个木偶。
我越操越起劲,双手掐着她的腰,汗水滴在她身上,她终于忍不住,低声咒
骂,「畜生……去死吧。」
我加快速度,鸡巴在她的体内搅动,感觉她的子宫在收缩,终于一股热流涌
出,我满意地灌满了她的里面,白浆从结合处溢出,顺着她的屁股流到床上。
我拔出来时,她的身体还在痉挛,但眼神依旧冷漠,没有一丝快感。
第二天早上,阳光洒进小院子,我懒洋洋地躺在床上,看着布林娅半裸着身
体,带着脚镣在房间里做家务。
脚镣的链子叮当作响,每走一步都提醒她自己的身份。
她弯腰擦地板时,那丰满的屁股翘起,骚逼和屁眼暴露无遗,后腰上还有她
奴隶身份的烙铁印。
我忍不住走过去,从身后抱住她,一只手伸到前面揉她的奶子,另一只手探
进她的腿间。
「别……停下,」她低声说,但身体已经软了,随便撩拨几下,下面就湿了。
我哈哈大笑,「停下?这是你的日常工作,骚货。」我手指插进她的骚逼,
搅动着,汁水溅出,她咬牙忍着,没迎合,但也没反抗。
我玩够了,就让她继续干活,不时走过去骚扰她一下,撩起裙子捏捏屁股,
舔舔奶头,看着她强忍的模样,心里满足极了。
我允许她按照她的基督教信仰做祷告,毕竟这能让她觉得活着还有点希望。
下午,她跪在墙角,双手合十,低声念着经文,那双蓝眼睛闭着,脸上是难
得的平静。
但我走过去,蹲在她身边,笑着说,「祈祷吧,宝贝。上帝能救你吗?」
她睁开眼,声音平静却带着绝望,我知道自己注定得不到她的心,但她的身
体已经完全归我所有。
我可以肆意奸淫玩弄她,每天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监视下。
她洗澡时我看着,她睡觉时我抱着,她甚至上厕所我都守在旁边。
起初她还会反抗,骂我,但渐渐地,被绝望感侵蚀的布林娅变得驯服,像只
被驯化的母狗。
但我清楚,这不是真心服从,她只是无处可逃。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逐渐不满足于简单的强奸。
那天,我从市场上买来灌肠用具,专门用来清洁肠道的,晚上我把布林娅按
在床上,四肢绑紧,她挣扎着,「你要干什么?别碰我那里!」
「闭嘴,贱货,」我冷笑,「今天玩玩你的屁眼。」
我把管子插进她的屁眼,注入温水和油,慢慢排空她的肠道。
她痛苦地扭动,脸红得像煮熟的虾,「啊……疼……你这个变态!」
排空后,她的屁眼干净光滑,褐色的小洞看起来很是诱人,我在她的屁眼上
抹上油,鸡巴对准那紧致的洞口,缓缓推进。
她尖叫起来,「不!停下!那里不是……啊!」
但她的身体顺从地张开,我开始抽插,鸡巴在她的屁眼里进出,感觉比骚逼
还紧致。
「操!你的屁眼真他妈会夹!」我吼道,一只手打她的屁股,啪啪作响。
她哭喊着,「撒旦的仆人!你会下地狱的!」
我越操越猛,最后射在她里面,白浆从屁眼溢出。
她瘫软下来,目光呆滞,但身体还在抽搐。
从那天起,我更变本加厉。
有一天,我把她按在我的大腿上,像打孩子一样,用手掌打她的屁股。
她的屁股丰满,弹性十足,每一巴掌下去都留下红印,她扭动着,「停下!
疼……你这个畜生!」
「疼?这是奖励,母狗,」
我大笑,「你不乖,我就打到你求饶。」
我打了几十下,她的屁股红肿,下面却湿透了。
我手指插进去搅动,她喘息着,「别……我恨你。」
但她的身体反应诚实,我满意地又操了她一顿。
我还试了更刺激的玩法。
把她双腿分开的倒着吊起来,用绳子绑在天花板的钩子上,她头朝下,奶子
垂着,骚逼大开。
我在她的骚逼里插上鲜花,一朵朵红色的野花塞进去,露出一截花茎,她羞
耻地哭喊,「拿出来!你这个疯子!这是亵渎!」
「亵渎?你的骚逼就是我的花园,」
我嘲笑,另一天换成蜡烛,点燃后插进去,蜡油滴在她里面,她尖叫,「烫!
啊……烧起来了!」
我看着她痛苦的样子,鸡巴硬了,直接操她的嘴,射在她喉咙里。
为了让她永远记住,我在大腿正面也烙印标记,一个我的符号,烫在她白嫩
的皮肤上。
每次她祈祷,跪下时就能看见那烙印。
她咒骂我是撒旦的仆人,我奖励她的子宫又一次被我的白浆灌满。
「骂吧,臭婊子,」
我边操边说,「你的子宫爱我的精液,它会吞下每一滴。」
布林娅逐渐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她不再大吵大闹,变得乖巧,但眼神里总有
那抹绝望。
我知道她只是无处可逃,而被迫适应和我在一起。
白天,我看着她拖着脚镣扫地,奶子晃荡,屁股扭动,不时走过去骚扰她,
捏她的奶头,拉她的骚逼唇,她顺从地张开腿,任我手指玩弄。
「主人……要操我吗?」她有时会低声问,但声音空洞,没有情感。
「对,骚货,」我把她按在桌子上,从后面插进去,鸡巴撞击她的屁股,啪
啪作响,「你的身体是我的,永远是!」
她喘息着,「是的……主人。」
但她的心,我知道,永远遥远。
日子就这样继续,我在阿尔及尔的小院子里,享受着这个金发奴隶带来的乐
趣。
有一天晚上,我又把她绑起来,玩她的屁眼,灌肠后直接操,她哭喊着,
「够了……我受不了了!」
「受不了?那就求我,」我吼道,鸡巴猛插。
她终于低声说,「求你……操我吧,主人。」
但她的眼神依旧呆滞,没有真心。
我射在她里面,满意地抱着她睡去,早上我看着她还没醒来的样子,觉得她
可爱极了,在她脸上亲了好一会儿,搂着她温暖丰满的身体,一种幸福满充满全
身。
白天时,我让她对我笑一下,布林娅依然冷着脸,尽量克制的对我说:「你
毁了我的家,却以为我会爱你吗?我的心永远不会属于你。」
【第一章·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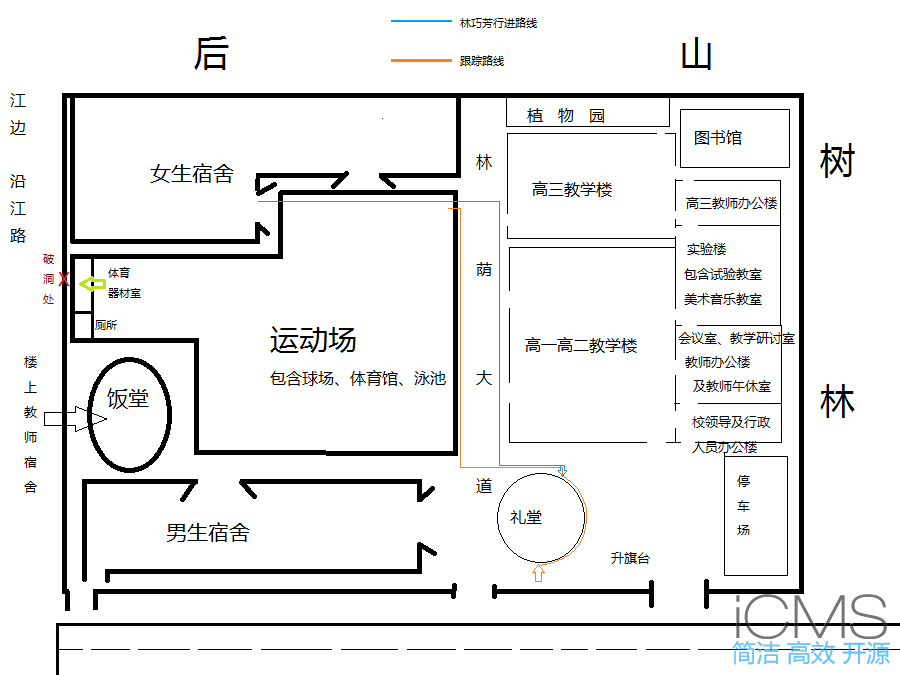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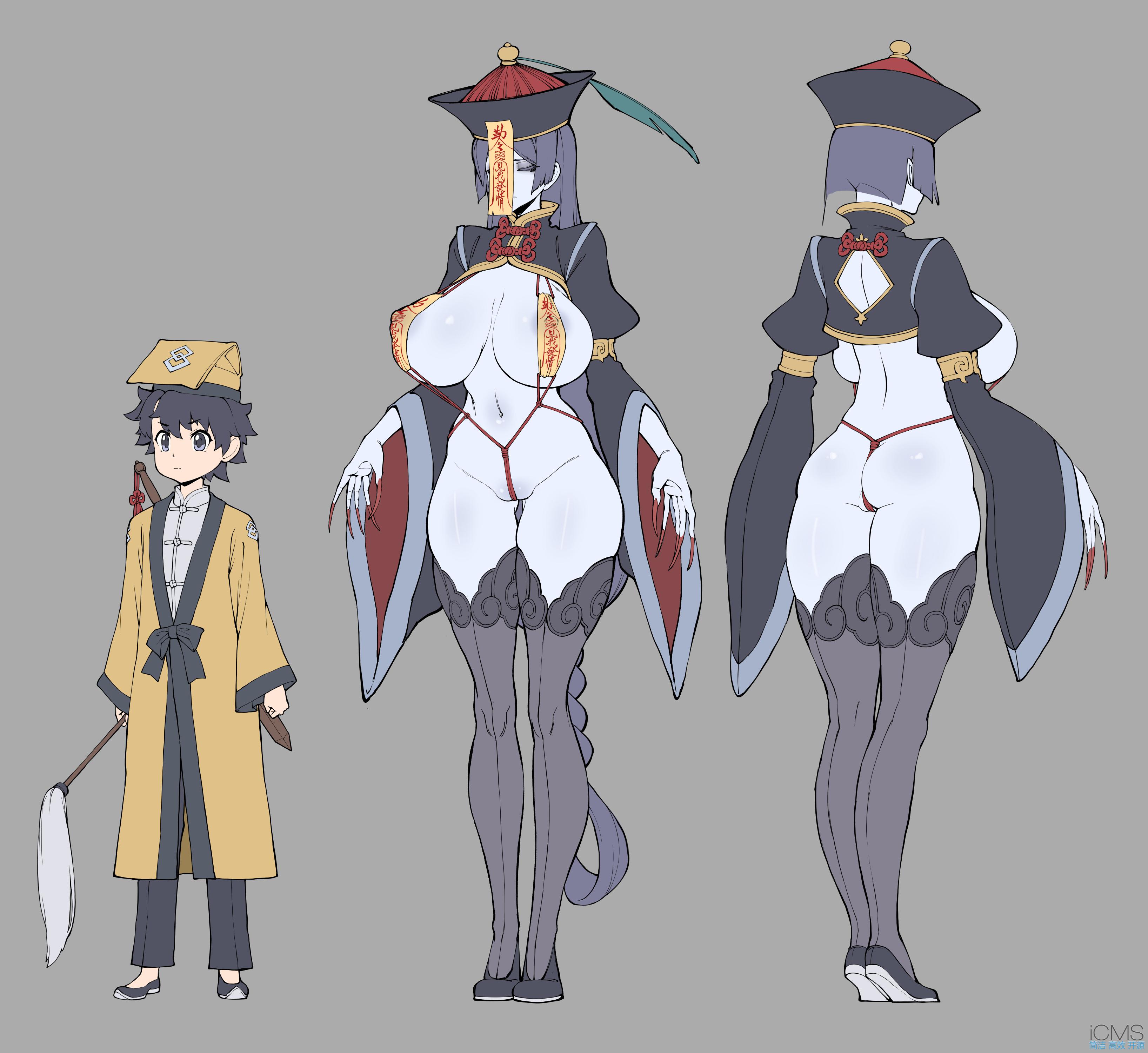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